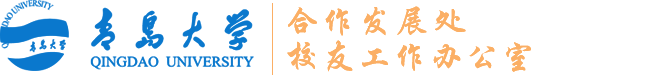乘车来到青岛市少年宫附近的青医职工宿舍,正要找人打听大门在哪儿时,忽然听见前方有人在楼上大声地喊我们。视线往上找,竟然正是我们的田老师。田老今年已经90岁了,声音仍然中气十足。待我们上了楼,田老和老伴儿早早地迎了出来,把我们让进了屋。田老的家不甚宽敞,没有专门的书房,书桌就摆在卧室的窗前,书桌旁倚墙处是一个大大的落地书橱,上面塞满了书,一摞摞的牛皮纸文件袋一直顶到天花板。
“那我们就从照片说起吧,”说着,田老拿过书桌上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将它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张摄于1956年的照片上留下的是医学院独立建院后第一次敲钟上课时的宝贵历史影像,照片背后还有田老师在63年前记录下的校刊刊登记录和照片内容解释。

田老捐赠了200多件像这种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老照片给学校综合档案馆,他说,“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其感人的故事,甚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而这些老照片的故事跟田老的一生是分不开的。
田老1956年由山东大学调入青岛医学院工作,从青岛医学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那刻开始,他就一直坚守在医学院的岗位上,一直见证着医学院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华岗,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的生物学家童第周,人体解剖学专家沈福彭,著名眼科专家潘作新,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提写“为革命服务”的医学专家魏一斋,喜好诗文、绘画与足球的内科专家杨枫……这些耳熟能详、甚至赫赫有名的专家教授都曾和田老师一起共过事,说起他们的故事,田老师的脸上多了笑容,他的娓娓讲述,让这些专家学者的形象在我们眼前立体和生动了起来。
田老和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束星北在崂山月子口水库劳动结束后调到青岛医学院,两人又再次同事。“文革”中,两人同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在松山路校区共同打扫厕所达三年之久,可谓同命运共患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需要整理一些老教授们的简历,名单中就有束星北。田老被安排整理束星北的档案。他来到束星北曾经工作过的海洋所想要寻找他的科研成就,但那么多的文件却都是束星北历年写的检讨。“我没办法摘取他的科学经历,只能一直跟随束星北进行记录,还访问了他的家人。”之后,田老先在院报上发表了题为《束星北:科学界的一位奇才怪才》的文章,之后陆续在《山东大学报》、《名人》月刊、《联合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束星北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等长篇通讯。文中,田老以无限深情写了真实而不平凡的束星北,“结缘相对论,走近爱因斯坦”“高尚师生情,钟爱李政道”,生动感人。束星北的故乡江苏邗江县派人到青岛采集束教授史料,还专门访问了田广渠老师,取得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束星北是天才物理学家,当时一起劳动的时候,哪里的进口仪器或者是复杂的机械设备坏了,都会请束星北去帮忙看看,只要他一看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儿”,田老说,“可惜他一生没有正式出版物,唯一的著作《狭义相对论》是他儿子在其死后两年才筹措出版的,如果束星北的才华和科研能力能用到他的专业上,我相信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抚摸着束星北儿子赠送的首版《狭义相对论》书稿,田老不无遗憾地追忆起了当年的这位老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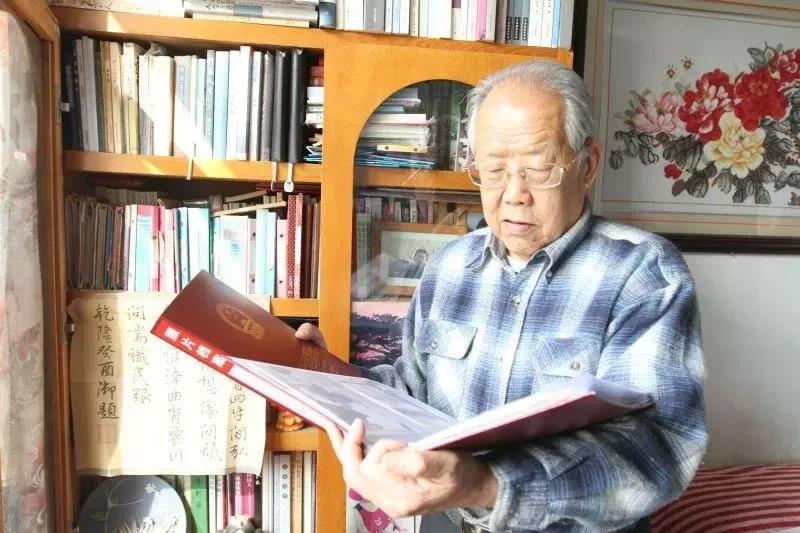
“还有魏一斋院长,1949年青岛解放后,上级委派他任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是唯一一位获得毛主席亲笔题字的医生,主席给他写下了‘为革命服务’几个大字。”田老颇有兴致地向我们介绍道。魏一斋在延安期间,担任过中央医院医务主任、院长,并一直兼任中央医科大学教师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大夫。田老说:“解放后中央派这么一个备受信任的干部来担任医学院院长,足以看到国家对我们医学院的重视。可惜我对他的记录还是太少了,我只保留了他与同学们照的一张集体照片,其他收藏的照片都是报纸上剪下的,很模糊。”
田老还搜集了许多沈福彭教授的资料,包括入党资料、党委批语,沈教授手写的英文病例和沈教授女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院搜集到的沈福彭读书时的资料等等。田老曾经为了撰写沈福彭的人物通讯,足足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调研各种资料。他与刘温和合作撰写的多篇文章,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传神地刻画了主人公丰富的精神世界,感人肺腑。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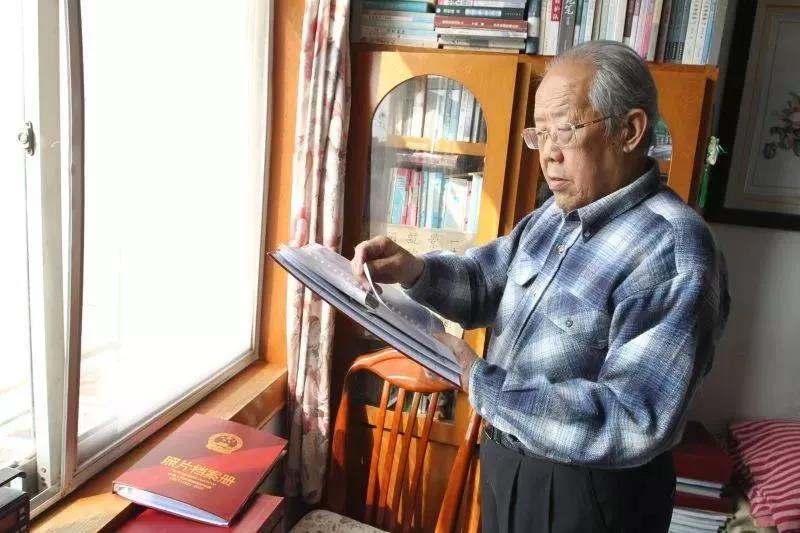
沈教授的学术水平与人品都值得我们大家敬重,我在给他撰写文章的时候保存了很多他的资料”,田老向我们介绍,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曾于1982年6月11日发出《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医学教授沈福彭同志学习的通知》,中央和省、市新闻媒介广泛报道了他的动人事迹 ,电视台还以沈福彭教授为原型拍摄了电视剧《夙愿》。“沈福彭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医学院的骄傲,他是第一位被山东省委省政府公开表扬并号召学习的大学教授。我建议我们学校档案馆能专门写一个沈福彭教授的纪念史。”
而谈起学院培养的人才、一直传承的优良学风以及曾经取得的各种科研荣誉,田老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当时医学院很多教授都是从欧美著名高校学成归国的学者,如沈福彭、潘作新、徐佐夏等等,他们治学严谨,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也非常高。
田老笑着告诉我们,当年因为沈福彭教授的考试太难通过,学生背后还曾埋怨过他。医学院1946年首次招生时,有56位学生入学,但是1952年却只有16名学生顺利毕业,“这其中除了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学院的要求非常严格,淘汰率极高。”这16名首届医学院毕业生后来分布在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河北、辽宁6个省市,都在各自的岗位为我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退休后很多年轻教师告诉我,医学院的学生们晚上不到熄灯时间是不会回宿舍待着的。
田老觉得,医学院几十年的优良学风一定要发扬光大,不要湮没了。校风和学风绝对会影响一个学生,读书风气浓、刻苦学习和在大学混上几年的差别太大了,无形的财产对于学生来讲是终生受益的。谈起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谈起医学院的毕业生已经遍布世界和全国各地,为医疗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田老师的语气中满是骄傲,“1978年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医学院就拿到了三个全国奖项,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1956年青岛医学院刚刚建院的时候,全国开始招收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即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医学院就有两个专业有招生资格,这是非常难得的。”

田老妥善保存着自己作为校刊编辑时校报刊登的每一张照片,自己和采访对象及其家人的每一封来往信件,他仍然保持着与华岗、束星北、童第周、王烬美家人的通信联络。田老将所有的记录与积累都分门别类地收藏在信封和文件袋中,他家里收集的各种采访和档案报纸资料,占满了两个大书柜。
对于记录,田老也特别严谨,我们注意到在每一张照片背面他都标记了当时在报纸上发表时的编号,在他书桌左手边抽屉中收藏着上百个整齐的纸封,里面存放的是他写文章时用过的资料。在田老这里,收藏与记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融入在生命的点滴里。那个年代也以文字的方式长存于田老的纸封。在文字质朴地低鸣中,感受到了“记着”对于记者来说独特的意义。
田老1991年退休,退休后花了三年时间与另外两位同事一起编写了《青岛医学院院志(1946—1995)》,“院志的资料来源于校报、档案,这里面的每篇资料出自哪里、第几页,我都有记录,这个东西不能糊弄。”田老的手指摩挲过院志的目录,从第一届医学生在小礼堂中的毕业典礼到教授们在运动会上的风采,这本院志仿佛封存了那50年的时光。
在最后将要离开的时候,田老对我们说:“我和医学院的缘分已经有68年了,进入90岁,突然有了紧迫感,希望把我记忆中的、我保存的那些人和事都写下来,把我们的青大故事更多地记录下来,这个抽屉里一个个信封都是我准备的材料,我很希望继续写文章,可惜眼睛不给我撑腰了……”
望着田老的背影
能够深深感受到学校的炙热的真挚的热爱
这种真挚是每位青大人所要传承的一种精神
眼睛不给您撑腰
阿浮和各位青大人来给您撑